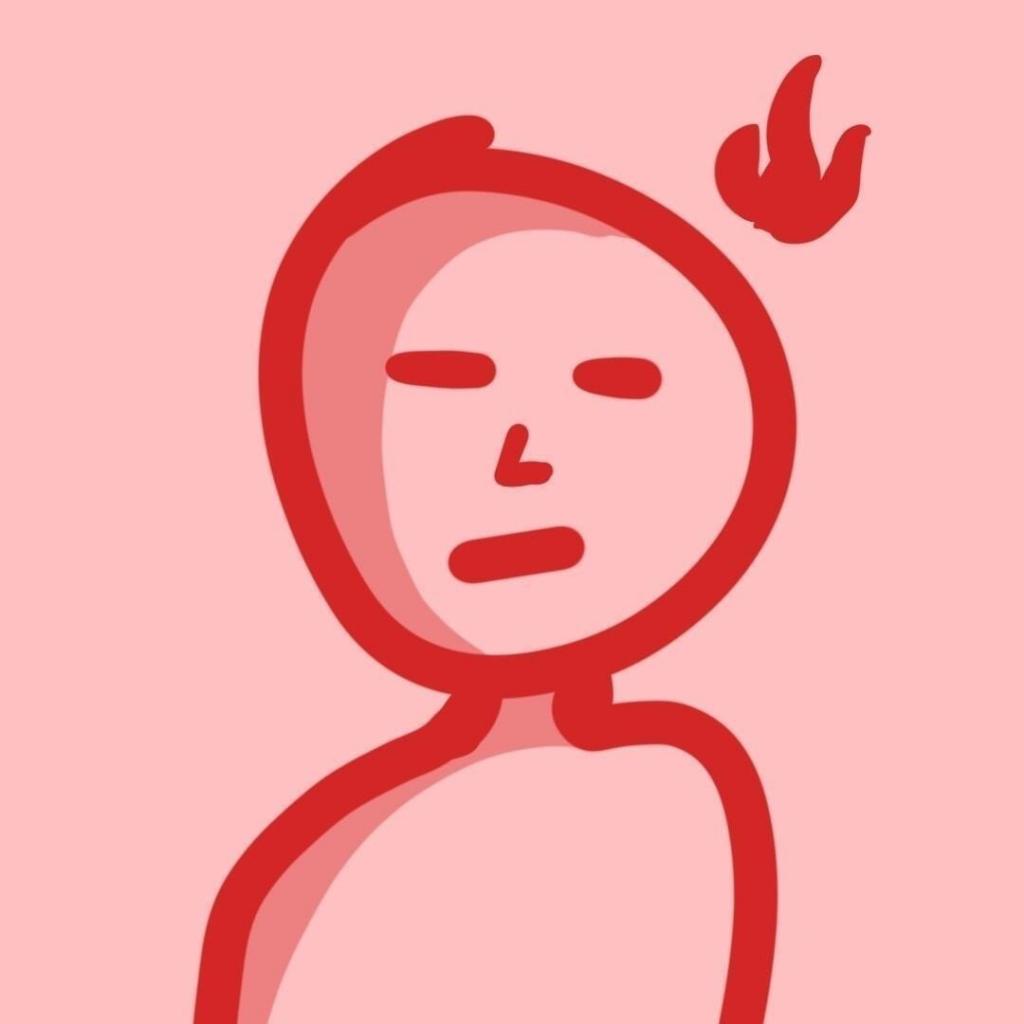 瑞瑞爱吃桃
瑞瑞爱吃桃 -
第1段写景有什么作用?
概括美女的特点。
“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说明忧伤的原因
 北营
北营 -
中外名作鉴赏与评析:《美女》
契诃夫
【题解】
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大师、杰出的戏剧家。他出生在一个未入等级的小商人家庭,童年生活困苦,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没有童年生活。”中学时代的契诃夫厌恶当时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大部分时间用于自学和研究戏剧。1880年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成为名医生。为了赚钱养家和供自己上大学,契诃夫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医生的职业使他熟悉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扩大视野,陶冶精神,对他的文学活动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契诃夫早期作品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以敏锐的洞察力、机智的气势、讥讽的笔触,妙笔生花地向所有的社会阶层开战,揭露小市民庸俗习气和卑劣愚昧的奴性心理,启迪人们为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而斗争。1885年以后,契诃夫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代表作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契诃夫一生创作了470多篇小说,代表作有:《草原》、《套中人》、《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万卡》等。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文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1版。
一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一块从顿河区大克列普卡雅乘车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村庄吗?我们停下来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美尼亚人家里喂马。像这么滑稽可笑的亚美尼亚人,这辈子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试想:一个秃亮的小脑袋,两道浓浓的八字眉,鹰钩鼻子,花白的长胡髭,一张大嘴,叼着一杆樱桃木的长烟袋;那小脑袋笨拙地粘在瘦削、伛偻的躯体上;身穿一套古怪的服装,特短的红上衣,特肥的浅蓝灯笼裤;此人走路八字脚,鞋底擦地沙沙响,说话的时候嘴里的烟袋不取出来,但一举一动都流露出纯亚美尼亚人的自尊感:从不微笑,两眼总是瞪得溜圆,尽量不去理睬自己的客人。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既没有见,也没有灰尘,可是令人感到像在大草原赶路一样不舒服,憋闷,无聊。记得,我满身尘土,热得浑身乏力,坐在屋角的一口绿色的大箱子上。没有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我知道,人们把茶炊端上来得用个把钟头,爷爷喝茶不会少于一个小时,然后他躺下睡两三个小时,这样我就得白等五六个小时,然后又是炎热、灰尘、路上的颠簸。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感到,那亚美尼亚人、那茶具橱、那些苍蝇、那被炎阳照射的窗子,我已经看了好久好久,要不再看见它们得到遥远遥远的将来,于是我对草原、太阳、苍蝇等等便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一个戴头巾的乌克兰女人送来一托盘茶具,然后又端来茶炊。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
“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光天化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一片乱云聚集在天边,太阳藏在它们的后面,把云和天空染成各种颜色:大红、橙黄、金黄、淡紫、玫瑰红;有的云状如修士,有的云像条鱼,还有像裹着头巾的土耳其人。霞光笼罩了三分之一的天空,辉映着教堂的十字架和地主宅邸的玻璃窗,反射到大河和水洼中,在树梢上抖动;一群野鸭就在这晚霞的辉映中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过夜去了……放牛的牧童,坐马车经过大坝的土地测量员,散步的老爷们,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而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莎足有一分钟,遂问道:
“这是您的女儿吗,阿维特u2022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上帝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莎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鬈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玛莎的白嫩脖颈以及她那青春的胸脯,虽然尚未发育成熟,但要想把它们雕塑下来,看来还非得有极高的创作禀赋不成。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莎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起初我感到伤心和羞愧,因为玛莎根本不理睬我,总是往下看;我似乎感到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又幸福又令人骄傲的气氛)把她和我隔离开来,并嫉妒地挡住了我的视线。
“这是因为,”我想,“因为我浑身是土,晒得黝黑,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
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忘记了我自己,全身心地沉湎于美的感受里。我再也不想草原的寂寞和尘土,再也听不见苍蝇的嗡嗡声,再也品不出茶的味道,只觉得桌子那边面对我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莎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为亚美尼亚姑娘本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莎。
喝完茶,爷爷躺下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这所房子跟巴赫契—萨拉赫所有的房子一样,坐落在太阳地儿里;没有树木,没有廊檐,没有阴凉。亚美尼亚人的大院长满滨藜和锦葵,尽管天热异常,却生机勃勃,充满欢乐。整个大院被一道道不高的篱笆墙隔成东一块西一块,在一道篱笆墙后正在打谷。打谷场的正中央立着一根柱子,套好的马一字排开,形成一个长长的半径,十二匹马绕着柱子转。旁边有个穿长坎肩和肥灯笼裤的乌克兰人,把长鞭子甩得啪啪响,大声吆喝着,那语调好像在戏弄马,跟它们耍威风似的:
“啊啊啊,该死的东西!啊啊啊……没有比你们更讨厌的了!害怕了吧?”
那些栗色马、白色马、花斑马不明白叫它们在一个地方转,揉碎麦草是为什么,便极不情愿地、仿佛吃力地跑着,感到委屈地摇着尾巴。风从它们的蹄子底下扬起了一团团金色谷壳的尘雾,然后又把它们远远地吹到篱笆外面去。在高高的新麦草垛旁边,有些妇女手拿耙子慢悠悠地干着,一辆辆大车在走动;在麦垛后的另一个院子里,也有同样的十二匹马绕着一根柱子转,也有一个乌克兰人把鞭子甩得啪啪作响,戏弄马匹。
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在稀疏的栏杆上和窗框上一些地方被晒得冒出了木胶;台阶下面和护窗板下面的细条阴影里有许多红色的瓢虫蜷缩着身子挤在一起。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莎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气愤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在她进去的门口出现一个驼背的老亚美尼亚女人,红脸膛,穿一条绿色灯笼裤。老太婆生气了,正在骂人。不大工夫玛莎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在大车后边不见了。赶马的乌克兰人放下鞭子,不吆喝了,向大车那边默默地看了好一会儿,后来,等亚美尼姑娘又在马的身边走过并跳越篱笆时,他用眼睛盯着她的背影,对马嚷叫着,那调子听起来仿佛非常伤心:
“叫你们不得好死,魔鬼!”
后来我总是经常不断地听到她光脚走路的声音,看到她严肃地、忧心忡忡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她顺台阶上上下下,经我身边带来阵阵轻风,或进厨房,或去打谷场,或到大门外,眼看她东跑西颠,弄得我来不及扭动脑袋。
她及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三个钟头的等候不知不觉过去了。我觉得我还没来得及细看看玛莎,卡尔波就已经跑到河边给马洗了澡并且套上了。一匹湿漉漉的马因洗得痛快喷着鼻子, 蹶子踢打车辕。卡尔波向它吆喝着:“捎一捎 [1]!”爷爷醒了。玛莎嘎吱一声把大门给我们打开了,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
两三个钟头之后,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
“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
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二
还有一回,即我正念大学的时候,我坐火车到南方去。那是五月。好像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之间的一个火车站,我走出车厢,在站台上散步。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连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罗斯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还没等我意识到什么,却忽然产生了在亚美尼亚村体验过的那种感觉。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魅人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它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罗斯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即使是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例如像亚美尼亚姑娘的那样,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是的,果然……”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气说。
至于“是的,果然……”是什么意思,我就不加评论了。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我、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军官走过车站的一个窗口,看到里边电报机旁坐着一个脸色苍白、头发发红的电报员,鬈发蓬松,颧骨突出而无出血,便叹气,说道:
“我敢打赌,这电报员一定爱那好姑娘。生活在天地间同一屋檐下,与这个轻盈的人物在一起而不相恋——岂不超越了人的力量。然而,我的朋友,如果你拱腰驼背、蓬头垢面、单调乏味、品行不端、滑头滑脑,爱上这对你并无好感、俊俏而愚昧的小姑娘,将是怎样的不幸,怎样的嘲弄啊!或许事情会更糟:试想,这个电报员堕入情网,同时却早已婚配,而他的妻子同他本人一样也是个拱腰驼背、蓬头垢面、品行不端的人……那真是苦透了!”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时靠着乘降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驰,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绒绒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赏析】
这是一篇奇特的小说,似乎不是一篇小说,而是一篇抒情色彩很浓的散文。小说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完整情节,就连主题也极朦胧微妙。小说以两个片断连缀在一起,分别抒写了“我”少年、青年时代看见两个美女时的感受——“一种虽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不单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周围的人们。这真是一种极其奇妙的感受!对于这种忧伤,小说中是这样解释的——“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小说中还这样写道——“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为亚美尼亚姑娘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回来。”这“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是什么?那神奇莫名的忧伤又为什么?或许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吧。即使我们真的参悟不透小说的真实意蕴,这一份伤怀之美也足以将我们深深打动。
契诃夫小说通常没有完整紧凑的故事情节,它只抓住生活的一个横截面或一个点来写,却能传达出生活背后极其丰厚的意蕴内涵,看似简短松散,实则灵巧精美,别有一番诗意美,本篇即是如此。同时这篇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色表现在对美女的刻画上。人的美是难于状写的,正面去写,往往会出力不讨巧。这篇小说写美女之美就没有正面写,而是运用多种手段(如对比反衬、虚写、比拟)去刻画美女带给人的微妙的心理感受,细腻传神,引人遐想。譬如,看到美女前,“我”对一切感到怨恨,烦闷不堪;看到美女时,却感到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吹散了种种苦闷,又有愉快而痛苦的忧伤;离别美女后,一连两三个钟头大家闷闷不乐,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这样特殊的印象式描写带给读者真切、鲜活的感受。
 Troublesleeper
Troublesleeper
-
黄昏的阴影已经投在车站的小花园里,月台上,旷野上。 火车站遮住西下的夕阳,不过从火车头里冒出来一团团烟,那最上面的烟带着柔和的粉红色,这就可以看出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我在月台上散步,发觉大多数散步的乘客老是在二等客车一个车厢附近走动和站定,从他们的神情看来,好象那个车厢里坐着一个有名的人物。我在这个车厢旁边遇见的好奇者当中,除了别人以外,还有一个跟我同车的旅客,他是个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可爱,就跟所有那些我们在旅途上偶然相识,不久又走散的人一样。 “您在这儿看什么?”我问。 他什么话也没回答,光是往一个女人那边丢了个眼色。那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年纪十七八岁,穿一身俄罗斯民族服装,头上没有戴帽子,肩膀上随随便便地搭一块小披肩。她不是车上的乘客,多半是站长的女儿或者妹妹。她站在那个车厢的窗子旁边,跟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乘客谈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我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心里就突然生出先前在亚美尼亚人的村子里体验过的那种感情。 这个姑娘美极了,不管是我还是那些跟我一块儿瞧着她的人,对这一点都毫不怀疑。 如果照通常的方式把她的相貌一样一样拆开来描写,那么她真正漂亮的地方只有她那一头波浪般起伏的、浓密的淡黄色头发,那些头发披散下来,用一根黑丝带扎住,至于那张脸的其余各部分,就或者是不端正,或者是十分平常了。她的眼睛总是眯得很细,这是由于她已经养成一种特殊的卖弄风情的习惯,或者由于近视。她的鼻子微微往上翘着,她的嘴很小,她那张脸的侧面轮廓软弱无力,她的肩膀窄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然而这个姑娘却给人留下真正的美人的印象。 我瞧着她,就不能不相信:俄国人的脸要显得美丽并不需要具有严格端正的五官,不仅如此,如果这个姑娘没有她那个狮子鼻,而换上另一个端端正正、完美无缺的鼻子,象那个亚美尼亚姑娘一样,那么她的脸似乎还会因此失去它所有的妩媚呢。 姑娘正站在窗前谈话,由于黄昏的潮气而缩起身子,不时回头看我们一眼,一忽儿双手插着腰,一忽儿把一只手举到头上,理一下头发。她又说又笑,脸上时而做出惊讶的神情,时而现出害怕的样子,我记得她的身体和脸一忽儿也没安静过。她那美的秘密和魅力恰好完全在于这些琐碎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在于她脸容的变化,在于她对我们投来的迅速的一瞥,在于这些动作的细腻优雅正好跟她的年轻娇嫩相配,跟她在笑语声中透露出来的纯洁灵魂相配,跟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为我们十分喜爱的那种脆弱相配。 这是蝴蝶的那种美丽,跟圆舞曲、花园里的闲游、笑声、欢乐十分相称,而跟严肃的思想、悲伤、安宁就格格不入了。 似乎,只要月台上刮过一股大风,或者下上一场雨,这个脆弱的身体就会突然萎缩,这种变幻莫测的美丽就会象花粉那样消散了。 “是啊,……”在第二遍钟声响过以后我们向我们的车厢走去的时候,军官叹了口气,嘟哝道。 至于这个“是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打算来推敲了。 也许他感到忧郁,不想离开那个美人和春天的黄昏而走进闷热的车厢去吧,或者,他也许跟我一样无端地怜惜那个美人,怜惜自己,怜惜我,怜惜所有那些懒洋洋地勉强走回 自己的车厢去的乘客吧。我们走过车站的一个窗口,看见里面有个脸色苍白、头发火红色的电报员坐在电报机旁边,他的鬈发高高地蓬松着,颧骨突出的脸黯淡无光。军官叹了口气,说:“我敢打赌,这个电报员爱上了那个漂亮的姑娘。生活在旷野上,又跟这么一个轻盈美妙的人儿住在同一所房子里,要想不爱上她,那可得有超人的力量才行。可是,自己是个背有点驼、蓬头散发、平淡乏味、品行端正而不愚蠢的人,却爱上一个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而且有点愚蠢的漂亮姑娘,我的朋友,这是什么样的不幸,什么样的嘲弄啊!或者,事情也许更糟,您不妨设想一下:这个电报员爱上了这个姑娘,同时他却已经结过婚,他的妻子跟他一样背有点驼、蓬头散发、为人正派。……那可真苦了!” 在我们车厢附近站着一个列车员,把胳膊肘倚在小广场的栅栏上,眼睛往美人站着的那边望。他那憔悴而肌肉松弛的脸浮肿而难看,由于夜间不得睡眠,又经受车厢的颠簸,一 直显得疯乏不堪,这时候却表现出感动和十分忧郁的神情,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见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看见了自己的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在懊恼,他整个身心都感觉到这个姑娘不是他的,他已经过早地苍老,粗俗而臃肿,因此他跟普通的、人类的、乘客们的幸福的距离已经象他跟天空那样遥远了。 第三遍铃声敲过,火车头的汽笛响起来,火车就懒洋洋地开动了。我们的窗外先是闪过验票员,站长,然后是花园,那个美人以及她那好看的、象孩子般调皮的笑靥。……我伸出头去,往后看,瞧见她用眼睛跟踪这列火车,在月台上走着,经过里面坐着电报员的那个窗口,理一下头发,跑进花园里去了。火车站不再挡住西边的天空,旷野就袒露在眼前,然而太阳已经落下去,一团团黑烟笼罩在绿油油、象丝绒般的冬麦地上。春天的空气也好,黑下来的天空也好,车厢里也好,都显得那么忧郁。 一个熟识的列车员走进车厢里来,动手点燃蜡烛。
我也很喜欢这篇文章。高中时做阅读时遇到的,老师讲的很动情。我读到 人们莫名的忧伤起来 那一段时,也莫名的忧伤起来了。
 LuckySXyd
LuckySXyd -
我很喜欢契科夫 也看了他很多篇文
我都不知道有这篇 会不会名字不对
中篇还是短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