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鱼炖火锅
大鱼炖火锅 -
没有白话详说,已接近白话。
芥子园画谱
青在堂画学浅说
鹿柴氏曰:论画或尚繁,或尚简,繁非也,简亦非也,或谓之易,或谓之难,难非也,易亦非也,或贵有法,或贵无法,无法非也,终于有法更非也。唯先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有法之极归于无法,如顾长康之丹粉洒落,应手而生绮草,韩斡之乘黄独擅,请画而来神明,则有法可,无法亦可,唯先埋笔成冢,研铁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后嘉陵山水。李思训屡月始成,吴道元一夕断手,则曰难可,曰易亦可,惟胸贮五岳,目无全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驰突董巨之藩篱,直跻顾郑之堂奥,若倪云林之师右丞,山飞泉立,而为水净林空,若郭恕先之纸鸢放线,一扫数丈,而为台阁牛毛蚕丝,则繁亦可,简亦未始不可,然欲无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难,欲练笔简净必入手繁缛,六法,六要。六长,三病,十二忌,盖可忽乎哉!
六法
南齐谢赫曰气运生动,曰骨法用笔,曰应物写形,曰随类写彩,曰经营位置,曰传摸移写,骨法以下五端可学而成,气运必在生知。
六要六长
宋刘道醇曰,气韵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变异合理三要也,彩绘有泽四要也,去来自然五要也,师学舍短六要也。
粗卤求笔,一长也,僻涩求才,二长也,细巧求力,三长也,狂怪求理,四长也,无墨求染,五长也,平画求长,六长也。
三病
宋郭若虚曰:三病,皆系用笔。一曰板,板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物状平褊,不能圆浑。二曰刻,刻者,运笔中疑,心手相戾,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三曰结,结者,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畅。
十二忌
元饶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忌远近不分;三忌山无气脉;四忌水无源流;五忌境无夷险;六忌路无出入;七忌石只一面;八忌树少四枝;九忌人物伛偻;十忌楼阁错杂;十一忌滃淡失宜;十二忌点染无法。
三品
夏文彦曰: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未知,神品;笔墨超绝,传染得宜,意趣有异者,谓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是规矩者,谓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成论也,唐朱景真于三品之上,更增逸品。黄休复作先逸而后神妙,其意则祖于张彦远,彦远之言曰,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谨细,其论顾奇矣!但画至于神能事已毕,只有不自然者,逸则自应置三品之外,岂可于妙能议优劣?若失于谨细,则成无非无刺,媚俗容悦而为,画中之乡愿与媵妾,吾无取焉?
分宗
禅有南北,二宗于唐始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于唐始分,其人实非南北也,北宗则李思训父子,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伯骕,以至马远、夏彦之。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澹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马驹云门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画传。而深于绘事者,代不乏人,兹不能具载,然不惟其画,惟其人,因其人,想见其画。令人亹亹起仰止之思者,汉则张衡、蔡邕;魏则扬修;蜀则诸葛亮;晋则嵇康、王羲之、王廙、王献之、温峤;宋则逺公;南齐则谢蕙连;梁则陶弘景;唐则庐鸿;宋则司马光、朱熹、苏轼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关、巨、董以异代齐名,成四大家后,而至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南渡四大家,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为元四家,高彦敬、倪元镇、方方壶,虽属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谓诸大家者,不必分门立户而门户自在,如李唐则远法,思训、公望则近守董源,彦敬则一洗宋体,元镇则首冠元人,各自春秋,赤帜难拔,不知诸家肖子,今日属谁?
能变
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元一变也,山水则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
鹿柴氏曰:赵子昂居元代而犹守宋规,沈启南本明人而俨然元画,唐王洽若预知有米氏父子而若泼墨之关钥先开,王摩诘若逆料有王蒙而渲澹之衣钵早具,或创於前,或守於后,前人恐后人之不善变而先自变焉,或后人更恐后人之不能善守而坚自守焉,然有胆不变者亦有识。
计皴
学者必须潜心毕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学既成,心手相应,然后可以杂采旁收,自出炉冶,陶铸诸家,自成一家。后则贵于浑忘,而先实贵于不杂。约略计之:
披麻皴、乱麻皴、芝麻皴、大斧劈、小斧劈、云头皴、雨点皴、弹涡皴、荷叶皴、矾头皴、骷髅皴、鬼皮皴、解索皴、乱柴皴、牛毛皴,更有披麻而杂雨点,荷叶而搅斧劈者。至某皴创自某人某人马牙皴,师法于某,余已具载于山水分图之上,兹不赘。
释名
淡墨重叠,旋旋而取之曰斡。淡以铳笔横卧惹而取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衮同泽之曰刷。以笔直往而指之曰捽。以笔头特下而指之曰擢。擢以笔端而注之曰点;点施于人物,亦施于苔树。界引笔去谓之曰画;画施于楼阁,亦施于松针。就缣素本色萦拂以淡水而成烟光,全无笔墨踪迹曰染。露笔墨踪迹而成云缝水痕曰渍。瀑布用缣素本色,但以焦墨晕其旁曰分。山凹树隙,微以淡墨滃溚成气,上下相接曰衬。
说文曰:“画畛也,象田畛畔也。”释名曰:“画挂也,以彩色挂象物也。”尖曰峰,平曰顶,圆曰峦,相连曰岭,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间崖下曰岩,路与山通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夹水曰涧,山下有潭曰濑,山间平坦曰坂,水中怒石曰矶,海外奇山曰岛,山水之名,约略如此。
用笔
古人云:“有笔有墨。”笔墨二字,人多不晓,画岂无笔墨哉。但有轮廓,而无皴法,即谓之无笔;有皴法,而无轻重向背云影明晦,即谓之无墨。王思善曰:“使笔不可反为笔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语是笔亦是墨。
凡画有用画笔之大小蟹爪者,点花染笔者,画兰与竹笔者,有用写字之兔毫湖颖者,羊毫雪鹅柳条者,有惯倚毫尖者,有专取秃笔者,视其性习,各有相近,未可执一。
鹿柴氏曰:“云林之仿关仝,不用正峰,乃更秀润,关仝实正峰也。李伯时书法极精,山谷谓其画之关钮,透入书中,则书亦透画中矣。钱叔宝游文太史之门,日见其搦管作书,而其画笔益妙。夏咏与陈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于临文,见草,而竹法愈超。与文士熏陶实资笔力不少。又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晔如。徐文长醉后拈写字败笔,作拭桐美人,即以笔染两颊。而丰姿绝代,转觉世间铅粉为垢,此无他盖其笔妙也。用笔至此,可谓珠撒掌中,神游化外。书与画均无歧致。不宁惟是,南朝词人直谓文为笔。沈约传曰:“谢元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庾肩吾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夫同此笔也,用以作字作诗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痒处,即抓着自己痒处。若将此笔,作诗作文与作字画,俱成一不痛不痒,世界会须早断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泼墨审成画。夫学者必念惜墨泼墨四字于六法三品,思过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旧墨,只宜书画纸,仿旧画,以其光芒尽敛,火气全无,如林逋、魏野具属典型久宜并席,若将旧墨,施于新缯,金笺金笔之上,则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旧墨之不佳也,实以新楮缯难以相受,有如置深山有道之淳古衣冠于新贵暴富座上,无不掩口胡虑臭味何能相人,余故谓旧墨留书,旧纸新墨,用画新缯金楮,且可任意挥洒,不必过惜耳。
重润渲染
画石之法,先从淡墨起可改救,渐用浓墨者为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画建康山势,先向笔画边皴起,然后用淡墨破,其深凹处,着色不离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谓之矾头,山中有云气,皴法要渗软,下有沙地,用淡墨扫屈曲为之,再用淡墨破。
夏山欲雨,要带水笔晕开,山石加谈螺青于矶头更觉秀润,以螺青入墨或藤黄入墨画石,其色亦浮润可爱。冬景借地为雪,以薄粉晕山头,浓粉点苔,画树不用更重,干瘦枝脆,即为寒林,在用谈墨水重过加润之,则为春树。
凡画山着色与用墨,必有浓淡者,以山必有云影,有影处必晦,无影有日色处必明,明处淡,晦处浓,则画成俨然云光日影浮动于中矣!
山水家画雪景多俗,尝见李营丘雪图,峰峦林屋,皆以淡墨为之,而水天空处,全用粉填,亦一奇也。
凡打远山,必先香朽其势,然后以青以墨一一染出,处一层色淡,后一层略深,最后一层又深,盖愈远者得云气愈深,故色愈重也。
画桥梁及屋宇须用淡墨润一二次,无论着色与水墨,不润即浅薄。王叔明画有全不设色,只以赭石淡水润松身,略勾石廓,便风采绝伦。
天地位置
凡经营下笔,比留天地,何谓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主意定景,窥见世之初学,据尔把笔,涂抹满幅,看之添塞人目,已觉意阻,那得取重于赏鉴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长论画,以奇峰绝壁,大小悬流,怪石苍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岚满纸,旷如无天,密如无地为上。此语似与前论未合,曰:文长乃潇洒之士,却于极填塞中具极空灵之致,夫曰:旷若曰密,如于字缝早逗露矣。
破邪
如郑癫仙、张复阳、钟钦礼、蒋三松、张平山、汪海云、吴小仙,于屠赤水画笺中,直斥之为邪魔,切不可使此邪魔之气绕吾笔端。
去俗
笔墨间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宁有霸气毋有市气,滞则不生,市则多俗,俗犹不可侵染,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学者其慎旃哉。
设色
鹿柴氏曰:天有云霞,烂然成锦,此天之设色也;地生草树,斐然有章,此地之设色也;人有眉目唇齿,明皓红黑,错陈于面,此人之设色也;凤擅苞,鸡吐绶,虎、豹炳蔚其文,山雉离明其像,此物之设色也;司马子长援据《尚书》、《左传》、《国策》诸书,古色灿然,而成《史记》,此文章家之设色也;犀首张仪,变乱黑白,支辞博辨,口横海市,舌卷蜃楼,务为铺张,此言语家之设色也。夫设色而至于文章,至于言语,不惟有形,抑且有声矣。嗟乎!大而天地,广而人物,丽而文章,赡而言语,顿成一着色世界矣!岂惟画然。即淑躬处世有如所谓倪云林淡墨山水者,鲜不唾面,鲜不喷饭矣。居今之世,抱素其安施耶?故即以画论,则研丹摅粉,称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轻黄,亦山水之极致。有如云横白练,天染朱霞,峰矗曾青,树披翠厨,红堆谷口,知是春深,黄落车前,定为秋晚,岂非胸中备四时之气,指上夺造化之工,五色实令人目聪哉!
又曰:王维皆青绿山水,李公麟尽画白描人物,初无浅绛色也,昉于董源,盛于黄公望,谓之曰吴装,传至文、沈,逐成专尚矣。黄公望皴,仿虞山石面,色善用赭石,浅浅施之,有时再以赭笔勾出大概。王蒙多以赭石和藤黄着山水,其山头喜蓬蓬松松画草,再以赭石勾出,时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画人物可用滞笨之色,画山水则惟事轻清。石青只宜用所谓梅花片一种,以其形似,故名。取置乳钵中,轻轻着水乳细,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则顿成青粉矣。然即不用力,亦有此粉,但少耳,研就时倾入磁盏,略加清水搅匀,置少倾,将上面粉青撇起,谓之油子。油子只可作青粉,用着人衣服。中间一层是好青,用画正面青绿山水。着底一层,颜色太深,用以嵌点夹叶及衬绢背。是之谓头青、二青、三青。凡正面用青绿者,其后比以青绿衬之,其色方饱满。
有一种石青,坚不可碎者,以耳垢少许弹入,便研细如泥。墨多麻亦用此出俨栖幽事。
石绿
研石绿亦如研石青,但绿质甚坚,先宜铁椎击碎,再入乳钵内,用力研方细,石绿用虾背者佳,亦水飞三种,分头绿二绿三绿,亦如用石青之法。青绿加胶,必须临时,以极清水投入蝶内,再加清水温火上略溶用之,用后即宜撇去胶,水不可存之于内以损青绿之色,撇法用滚水少许,投入青绿内,并将此蝶子安滚水盆内,须浅不可没入,重汤顿之,其胶自尽浮于上,撇去上面清水则胶尽矣,是之谓出胶法。若不出尽,则次遭取用,青绿便无光彩。若用则临时再加新胶水可也。
朱砂
用箭头者良,次则芙蓉疋砂。投入乳钵中研极细,用极清胶水同清滚水倾入盏内,少顷将上面黄色者撇一处,曰朱标,着人衣服用,中间红而细者,是好砂,又撇一处,用画枫叶栏楯寺观等项,最下色深而粗者,人物家或用之,山水中无用处也。
银朱
万一无朱砂,当以银朱代之,亦必有标朱,带黄色者,水飞用之,水花不入选。
珊瑚朱
唐画中有一种红色,历久不变,鲜如朝日,此珊瑚屑也,宣和内府印色,亦多用此,虽不经用,不可不知。
雄黄
拣上号通明鸡冠黄,研细水飞之法,与朱砂同,用画黄叶与人衣,但金上忌用,金笺着雄黄,数月后即烧成惨色矣。
石黄
此种山水中不甚用,古人却亦不发,妮古录载石黄用水一碗,以旧席片覆水,碗上置灰,用炭火煅之,待石黄红如火,取起置地上,以碗覆之,候冷细研调,作松皮及红叶用之。
乳金
先以素盏稍抹胶水,将枯撤金泊,以手指蘸胶一一粘如,用第二指团团摩搨,待干,粘碟上,再将清水滴许,搨开屡干屡解,一极细为度,再用清水将指上,及碟上一一洗净,俱置一碟中以微火温之,少顷金沈,将上黑色水尽行倾出,晒干,碟内好金,临用时稍稍加极清薄胶水调之,不可多,多则金黑无光,又法将肥皂核内剥出白肉,溶化作胶,似更清。
传粉
古人率用蛤粉法,以蛤蚌壳煅过,研细,水飞用之,今闵中下四府垩壁,尚多用蚌壳灰,以代石灰,犹有古人遗意,今则画家,概用铅粉矣,其制以铅粉将手指乳细,醮极清胶水于碟心摩擦,待摩擦干,又醮极清胶水,如此十数次,则胶粉浑溶,搓成饼子,粘蝶一角晒干,临用时以滚水洗下,再清清滴胶水数点,撇上面者用,下者拭去,研粉必须手指者,以铅经人气,则铅气易耗耳。
调脂
谚云:藤黄莫入口,胭脂莫上手,以胭脂上手,其色在指上经数日不散,非用醋洗不退,须用福建胭脂,以少许滚水略浸,将两笔管如染坊绞布法,绞出浓汁,温水顿干用之。
藤黄
本草释名:载郭义恭广志,谓岳鄂等州,崖间海藤花叶败落石上,土人收之,曰沙黄,就树采拮,曰腊黄,今讹为铜苗,为蛇矢,谬也。又周达观直猎记云:黄乃树脂,番人以刀斫树,脂滴下次年收之者,其说虽与郭异,然皆言草木花与汁也,从无蟒蛇矢之说,但气味酸,有毒,蛀牙齿,贴之即落,舔之舌麻,故曰莫入口耳。当拣一种如笔管者,曰笔管黄,最妙。
旧人画树,率以藤黄水如墨内,画枝干,便觉苍润。
靛花
福建者为上,今日棠邑产者亦佳,以沤蓝不在土坑,未受土气,且少石灰,故色迥异他产,看靛花法,须拣其质极轻,而青翠中有红头泛出者,将细绢筛滤去草屑,茶匙少少滴水,如乳钵中,用椎细乳,干则再加水,润则又为擂,凡靛花四两,乳之必须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再加清胶水,洗净乳杵钵,尽倾入巨盏内澄之。将上面细者撇起.盏底色粗而黑者.当尽弃去。将撇起者置烈日中,一日晒干乃妙。若次日则胶宿矣。凡制他色,四时皆可。独靛花必俟三伏,而画中亦惟此色用处最多,颜色最妙也。
草绿
凡靛花六分,和藤黄四分,即为老绿,靛花三分,藤黄七分,即为嫩绿。
赭石
先将赭石拣其质坚而丽者为妙,有一种硬如铁与烂如泥者,皆不人选。选以小沙盆水研细如泥,投入极清胶水,宽宽飞之,亦取上层,底下所澄,粗而色惨者弃之。
赭黄色
藤黄中加以赭石,用染秋深树木叶彩色苍黄,自与春之嫩叶淡黄有别,如着秋景中,山腰之平坡,草间之细路,亦当用此色。
老红色
着树叶中丹枫鲜明乌柏冷却,则当纯用朱砂,如柿栗诸夹叶,须用一种老红色,当于银朱中加赭石着之。
苍绿色
初桑木叶,绿吹变黄,有一种苍老暗淡之色,当于草绿中加赭石用之,秋初之石坡土径,亦用此色。
和墨
树木之阴阳、山石之凹凸处,于诸色中阴处凹处处,俱宜加墨,则层次分明,有远近向背矣。若欲树石苍润,诸色中尽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层阴森之气,浮于丘壑间。但朱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余将诸件重滞之色,分罗于前,而以赭石靛花清静之品,独殿于后者,以见赭石靛花二种,乃山水家日用寻常有宾主之谊焉,丹砂石黛犹如峩冠博带揖让,雍容安得不居前席?有师行之法焉,凡出师以虎贲前功,羽扇幕后,则丹砂石黛皆虎贲也,又有德充之符马滓秽日以去清虚日以来,则赭石靛花又居清虚之府艺也,而进乎道矣。
绢素
古画,至唐初皆生绢,至周昉韩干后,方以热汤半熟,入粉,槌如银板,故人物精彩入笔。今人收唐画,必以绢辨。见文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张僧画、阎本立画,世所存者皆生绢。南唐画皆粗绢,徐熙绢或如布。宋有院绢,匀净厚密,有独梭绢,细密如纸,阔至七八尺,元绢类宋,元有密机绢,亦极匀净,盖出吾禾魏塘密家,故名,赵子昂盛子昭多用明绢内府者,亦珍等宋织。
古画绢淡墨色,却又一种古香可爱,破处必有鲫鱼口,连有三四线,不直裂也,直裂者伪矣。
矾法
绢用松江织者,不在铢两重,只拣其极细如纸,而无跳线者,粘帧子之上左右三边,帧下以竹签签之,以细绳交互缠帧,待上矾后,扯平无凹无偏,如绢长七八尺,则帧之中间宜上一撑棍,凡粘绢必挨大干方可上矾,未干则绢脱矣,矾时排笔无侵粘边,侵亦绢脱矣,即候干不侵粘处,因梅天吐水,而绢欲脱,则急以矾掺边上,又万一侵边而有处欲脱,则急以竹削鼠压钉钉之,矾法,夏月每胶七钱,用矾三钱。冬月每胶一两,用矾三钱。胶须拣极明而不作气者,近日广胶,多如麸面假造,不堪用。矾须先以冷水泡化,不可投热胶中,投入便成熟矾矣。凡上胶矾,必须作三次,第一次须轻些,第二次饱满,而青青之上,第三次则以极清为度,胶不可太重,重则色堵,而画成多冰裂之忧,矾不可太重,重则绢上起一层白铺,画时滞笔,着色无光落,绢背衬处亦然,矾时帧子宜立起,排笔自左而右,一笔挨一笔横刷,刷宜匀,不使其渍处,一条一条,如屋漏痕,如此细心矾成,即不画亦属雪净江澄,殊可缔玩,若画遇稍粗之绢,则用水喷湿,石上槌眼匾,然后上帧子矾。
纸片
澄心堂宋纸及宣纸,旧库疋纸楚纸皆可以任意挥毫,湿躁由我,惟宣纸中一种镜面光,及数揭而粗且薄之高丽纸,云南之砑金笺,与近日之灰重水性多之时则为纸中奴隶,遇之,即作兰竹,犹属违心也。
点苔
古人画多有不点苔者,苔原设以盖皴法之慢乱,既无慢乱,又何须挖肉做疮,然即点苔,亦须于着色诸,一一告竣之后,如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攒苔,亦自不苟也。
落款
元以前多不用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耳,至倪云林字法遒逸,或诗尾用跋,或跋后系诗,文衡山行款清整,沈石田笔法洒落,徐文长诗歌奇横,陈白阳题志精卓,每侵画位翻多寄趣,近日俚鄙匠习,宜学没字碑为是。
练碟
凡颜色碟子,先以米泔水温温煮出,再以生姜汁及酱涂底下,入火煨顿,永保不裂。
洗粉
凡画上用粉处微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即去。
揩金
凡金笺金扇上,有油不可画,以大绒一块揩之,即受墨矣。用粉揩固去油,但终有一层粉气,亦有用赤石脂者,终不若大绒之为妙也。
矾金
凡金笺起难画,及油滑胶滚,画不上者,但以薄薄轻矾水刷之,即好画矣。如好金笺画完时,亦当上以轻矾水,则付裱无件裂、粘起之患。
往余侍栎下先生,先生作近代画,人传亦曾闻道于盲,有所商榷,余退而成画董狐一书,自晋唐以迄昭代,或人系一传,或传列数贤,客有指为画海者,尚剞劂有待,兹特浅说俾初学耳,然后坡不惜笔舌诱掖不惟读书之士,见而了然尽理,即丹青之手,见而皇然读书客,曰:此有苗格也,余急掩其口,时已未古,重阳新亭客櫵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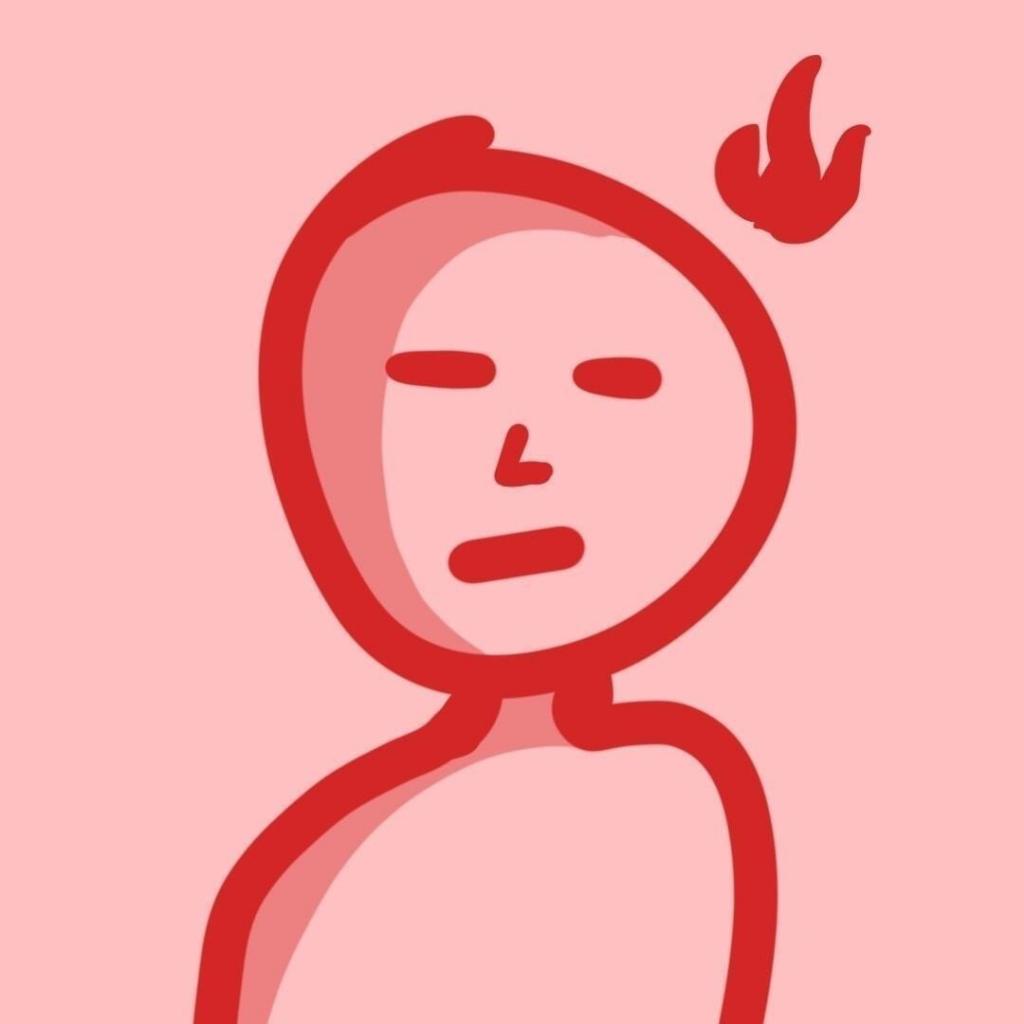 瑞瑞爱吃桃
瑞瑞爱吃桃 -
这个还是要有些文言文的功底的,既然这样--就放下这本书--现在的资讯这样发达--技法与理论书--多得是--
《芥子园画谱》--画法集大成者--是很不错的,但,“过”,便显得僵化,过于程式化了,再,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现在看来--是有很多的不令人满意的地方--,建议还是----
 寸头二姐
寸头二姐 -
没有白话本,也没有译文
其中的技法和各项事宜,现代画家们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运用到自己的画作中。精练的语言言传之,意会之,也就不译不白话,保《芥子园画谱》原状。
 臭打游戏的长毛
臭打游戏的长毛
-
自己看得不是很明白……能懂个大意,有似乎其实没有搞懂完...
